藻溪,那条母亲的河
——走进“雁过藻溪文化客厅”
陈瑞琳

高速的列车忽然就稳稳地停靠在温州南站,风里面立刻有了南方水乡的温热。拎着两个沉重的箱子下车,心脏砰砰地有些跳,年过半百的我,竟然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举世闻名的商都。听人说温州人是中国的犹太民族,其身影遍布世界,但我对温州人的亲近,却是从认识了一位温州籍的女作家开始,她的名字叫张翎。
眼前是温州南站的候车室,我要去的地方还在离温州不远的苍南。记得在窗口买车票的时候,我把“苍南”使劲念了两遍,还特别解释了怎样写,让那个售票的女人白了我一眼,显然是嫌我啰嗦。夹在熙攘的人群中,空气里传递着闽南的乡音,顿时感觉自己穿得有点多。我让自己镇定,因为有陌生感,就躲在大厅的边缘处,等待着那个去苍南的火车进站。
一面看着手机,一面在心里问自己:“如果不是张翎的那个《雁过藻溪》的小说,你会不会去藻溪?”答案是否定的,或许我终生都不知道这世界有个地方叫藻溪。文学就是有这么奇妙的力量,想想苏轼的《赤壁赋》,多少人在寻找赤壁,就像我现在,因为爱上了一部小说,万里迢迢回来,只为看一眼那个孕育了多少故事的苍南。
恍惚中手机有振动,一条微信跳进来:“你在哪里?我也在等火车,你往前走!”我彻底惊呆,完全没有预料,这怎么可能?那个发微信的人正是张翎,她竟是与我同班车去苍南。

记忆如光,飞速地穿梭到2008年。在《江南》杂志的第六期长篇小说专号上,张翎发表了她的获奖力作《雁过藻溪》,同期也发表了我的评论《穿越“紫东院”,碾碎“六月莲”》。张翎在小说的开头写道:“谨将此书献给母亲和那条母亲的河!”小说里的那条河,就是苍南县的藻溪。那个时候,我就设想着有朝一日,一定要去这个“有几分诗意的小乡镇”看看,最好是能跟着张翎一起去!11年过去,简直就是冥冥中的天意,这一刻真的来了,而且就是这么巧合,让我顿时欢喜到手脚忙乱。
跟在张翎的身后,享受了苍南的第一顿晚餐,见到了许多当地的、外地的朋友,时间与空间顿时亲切地交错在一起,尤其是那一盘全生的螃蟹,真是比酒还要醉人。夜里无眠,主要是盼着早点醒来,藻溪啊藻溪,你会让我失望吗?
期待的时刻终于到来,只是在转眼间,那条清澈的藻溪就恍然出现在了眼前,它很平静,波澜不惊,两岸很开阔,完全没有局促的狭窄,正是我多年猜想的,就是这样从容大气又不动声色地流向江河大海。

登上岸边的藻溪公园,脚下的小狮山并不雄伟,却很亲切,无论妇孺老少,都爬得上去。从公园往下看,与藻溪相连的整个城镇一览无余,错落有致的绝佳视野,风景好美。就在半山腰上,出现了一片开阔地,迎面是一个石砌的矮墙,古朴的四个大字“雁过藻溪”,深深地镶在墙上。驻足在它的面前,感觉这四个字仿佛已立在这里很久很久。墙的后面,就是已经改建好的“雁过藻溪”文化客厅。
仰头望去,一座现代风格的馆式两层建筑呈现在眼前。高大的客厅采用的是铁灰色金属框架,典雅庄重,配置着宽大的落地窗,透明清澈。心里顿时生出敬意,回看神州大地,无数奢华的仿古建筑,但能够以一部小说命名的文化客厅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,这需要的不仅仅是卓越的眼光,还更有深远的情怀。待我走进一楼的大厅,在素白的墙壁上印刻着有关张翎的创作资料,让我真是惊喜不迭,感叹自己研读张翎二十多年,竟然还有这么多未知的故事深藏在藻溪的砖缝之间。
这是11月16日的上午,也就是一转眼,“雁过藻溪文化客厅”呼啦就坐满了人,不得不佩服“苍南县知行读书会”这个民间组织,他们真是好厉害,把镇里镇外喜爱文学的人一下子召集在这里。这是一场关于“故土和家园”的文学论坛,也是一次国际视野的跨界对话,我们七位来自五个国家和地区的作家、学者,包括有澳门大学的朱寿桐教授,香港浸会大学的张宏生教授,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的孔书玉教授,温州大学的孙良好教授,以及云南作协主席范稳先生和我。记得张翎这样说: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占据一个人记忆和想象力最大空间的地方,就是文学意义上的故土。”以小说“西藏三部曲”闻名的范稳,他对乡土文化书写的理解,有着自己新颖的角度,他说:“故乡是用来回忆的,他乡是用来发现的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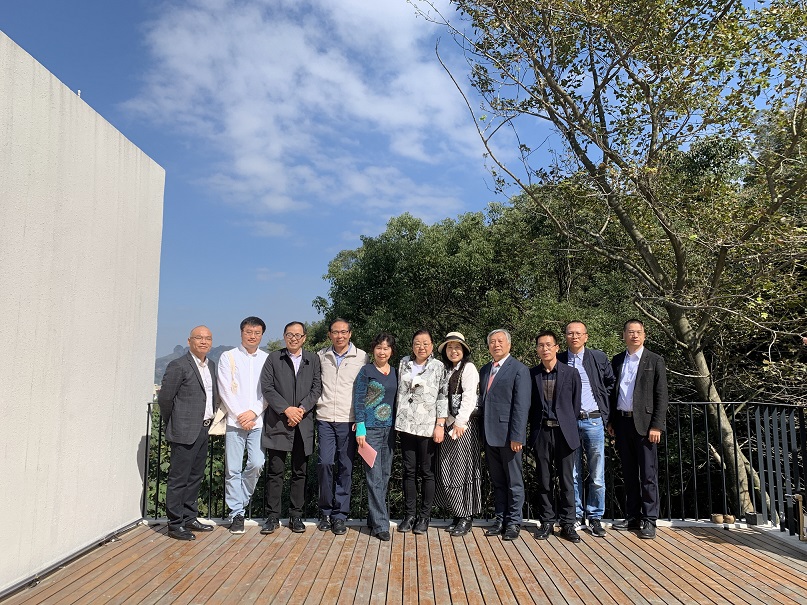
对于藏在深闺的藻溪镇来说,举办这样的跨国文学论坛,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创举。在海内外的文学界,人们大多知道作家张翎的老家在温州,但并不了解她的母亲是藻溪人,早在民国时期,张翎的外公就是藻溪最早留学东洋、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士。感谢张翎的母亲,在张翎的童年和少年,总是会告诉她有关藻溪的许多故事,正是这些故事,在张翎的心里撒下了种子,慢慢繁衍成她后来的文学花园。
据张翎回忆,1986年的夏天,在她即将启程出国留学时,第一次来到父母的原籍,为埋葬在那里的先辈们扫墓。那个曾经被她多次填在表格中的籍贯,终于有了直观的意义。藻溪是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,那里埋葬着爷爷、奶奶,还有许多叫得出和叫不出名字的亲戚。还有那条由明矾而生的挑矾古道,成就了藻溪当年的繁荣,也成就了张翎父亲和母亲的婚姻。

关于《雁过藻溪》的创作灵感,张翎说来自一段特殊的旅程,但她却是那段旅程中的缺席者,是母亲为她做了细致的填补:“那年我外公去世,他的骨灰在亲人的护送下由温州回归藻溪故里。在场的母亲通过越洋电话,对缺席的我详细叙述着那次旅途的种种细节。十里长亭的祭灵队伍,延续不断的鞭炮,身着丧服叩迎在桥头的乡亲……藻溪用最朴实诚挚的方式,接他们引以为傲的游子归家。母亲话语里的温热,通过越洋电缆传到我的耳膜上,放下电话时,我才觉出了脸颊上的泪水。就在那一刻,一部小说的灵感,开始在我的胸腔里涌动。”
《雁过藻溪》的故事是写一位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女科学家,因母亲病故而回到久违的故国,和女儿一起送骨灰回到母亲的老家,那个叫藻溪的地方,这个叫末雁的女科学家却因此发现了一桩母亲埋藏了一辈子的秘密。她的母亲黄信月,在少女时代即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,经受了丧失人性的折磨、羞辱,最终逃离火坑,却含辛茹苦隐忍了一辈子,至死也不敢暴露自己被损害污辱的真情。只能在遗言中反复交代,让女儿亲自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藻溪老家埋葬,希冀女儿能从中得到启示,最终明白自己的出身。小说有回忆、有插叙、有暗示、有感悟,一趟看似寻常的回乡葬母之行,却不亚于北极探险,作者以她的个性之笔,把大变动年代的一段情爱恩仇写得峰回路转、惊心动魄,可谓是谱写了一曲三代女性悲怆的咏叹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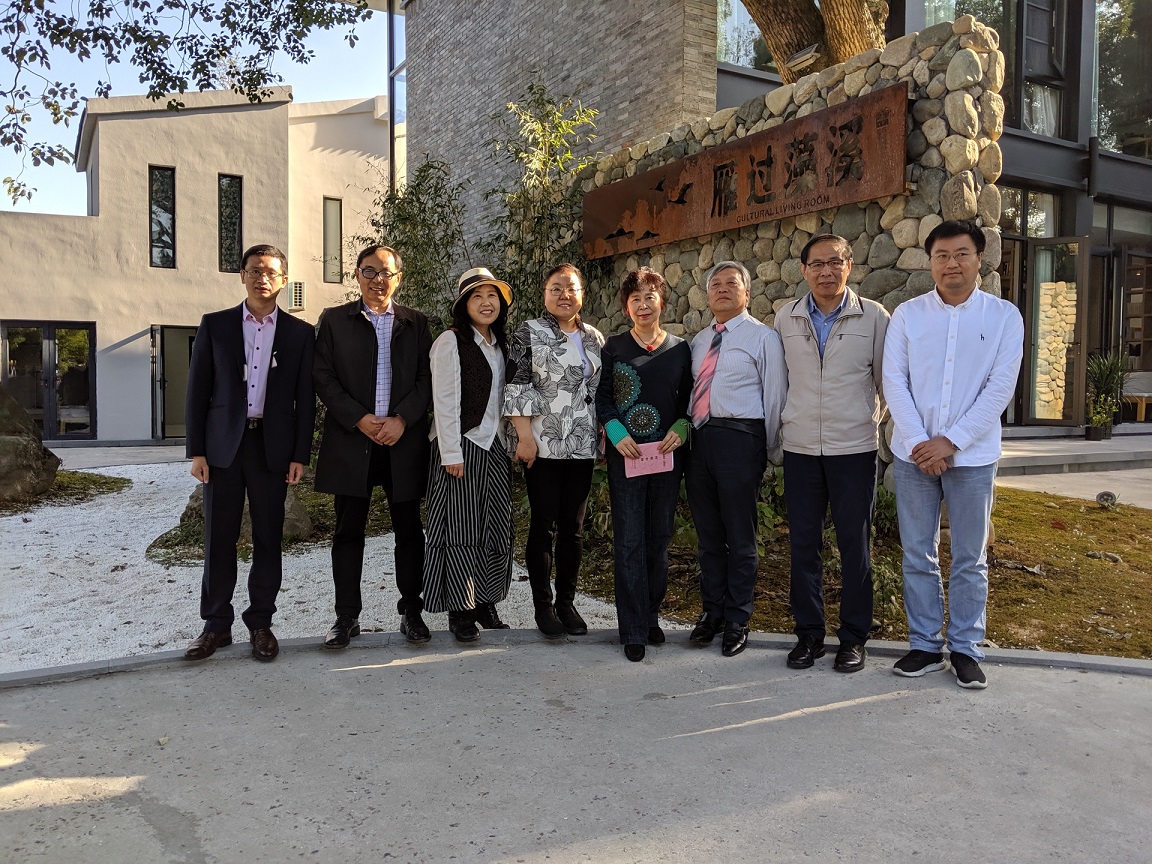
张翎在书中这样写道:“末雁走上台阶,站在厚厚的木门前,用指甲抠着门上的油漆。最上面的一层是黑色的,斑驳之处,隐隐露出来的是朱红。朱红底下,是另外一层的朱红。那一层朱红底下,就不知还有没有别的朱红了。每一层颜色,大约都是一个年代。每一个年代都有一个故事,末雁急切地想走进那些故事。”
“末雁咚的一声坐到了地上,捏着手绢捧着胸,仿佛心已经掉落在手绢上了。不知这手绢是不是母亲用过的?那上面的斑点,会不会是母亲留下的?泪也好,血也好,当年再鲜活的一段记忆,在五十年的风尘里走过一遭,剩下的不过是几个颜色和意义都很暧昧的斑点。若再等个五年十年,恐怕连这斑点也要消失,变成无形无体的一片混沌。”作者显然是在呐喊,用无声的手绢呐喊:母亲的历史不该被我们遗忘!
《雁过藻溪》无疑是张翎创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值得庆幸的是,就在《雁过藻溪》发表10余年之后,以“雁过藻溪”命名的文化客厅,真的就在依山傍水的藻溪公园落成。从母亲那一辈的记忆里生出的一簇灵感的火花,火花里生出了一部小说,一部小说里又生出了一个聚会的场所,从这个聚会的场所里,又生出了一丛丛文化启蒙的灯火,照着过去、今天还有未来。
随着这个文化客厅的落成,一群群心里点灯的人开始在这里相聚。藻溪镇的市民,尤其是镇里中学的学生和年青人,都爱上了这个地方。还有好多县城的市民和外县的阅读爱好者,也纷纷慕名前来。藻溪,这块曾经有着深厚文脉的土地,又吹起了一股新鲜的文学和文化之风。麦浪一样滚滚传递的“雁过藻溪文化客厅”,正在成为苍南县文化建设的一个独特品牌。
文化客厅的一楼是个大书吧,提供着公共图书馆的功能。但是,让我惊喜的却是文化客厅的二楼,竟有四个民宿的房间,分别以张翎的四部作品命名,有《望月》、《一个夏天的故事》、《流年物语》和《劳燕》。民宿的旁边还有一座辅楼,有一个大茶室和一个大阳台,只要凭栏瞭望,感觉就是江山如画。
就在那个迷人的午后,我们在“雁过藻溪文化客厅”的楼上民宿里小憩。我选择了《望月》,因为它是我当年读张翎的第一部作品,床头上悬挂的就是《望月》的封面,那么熟悉,那么亲切,感觉自己又重新回到了二十多年前,回到了当年的望穿秋水。

坐在窗前,看着藻溪流向敖江,流向大海。由此想到,张翎的小说都与“水”有关,从小溪到江河,再到大海。她自己说:“我的场景有时在藻溪,有时在温州,有时在多伦多,有时在加州,就是说一个人的精神永远‘在路上’。”她的小说里总是充满了流动的“水性”,这水既是透明的,也是伤痛的,如《唐山大地震》;既是柔软的,也是坚硬的,如《劳燕》,水滴石穿的顽强,构成了家国的风云。
喜欢张翎的小说,正是喜欢她以独具的冷峻目光,从择水而居的“乡土”中挖掘出不为人知的历史,又从历史中挖掘出丰富深邃的“人性”。她的精神骨髓里有一种“冷”,这是她对生命无常以及人世荒凉的深切感悟,她的文字里有特别的“暖”,来自她对鲜活世界情感源泉的呕心热爱,她还有一种心平气和的“静”,是因为她总能把自己远远地置身在滚滚的红尘之外。所以,张翎的小说才能传到久远。
重读《雁过藻溪》,心里充满感叹:文学,就是有如此强大的力量,苍南的藻溪,因为这篇小说将被很多读者记住。神秘温柔的藻溪,有了自己的文学家。张翎的名字正在走向世界,走向海内外更多的读者,藻溪这块土地,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永恒。
不断飞越的张翎,无论是在他乡的“寻找”,还是故土的“回归”,她一直都在探索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。未来的时光,人们或许去湘西的凤凰寻找沈从文的《边城》,或许也会来到苍南,寻找张翎的《雁过藻溪》。


